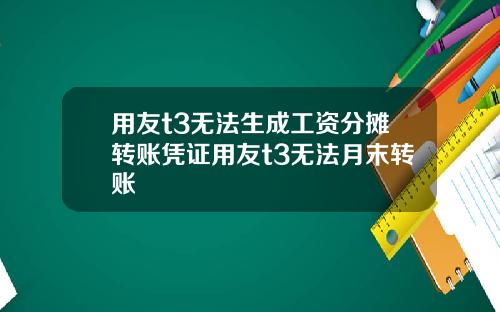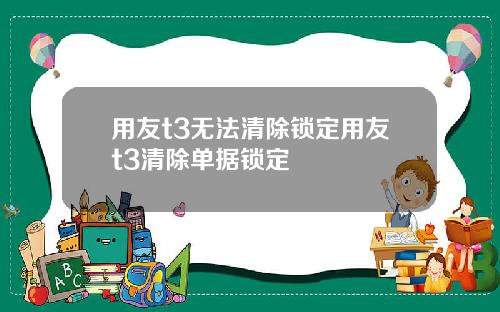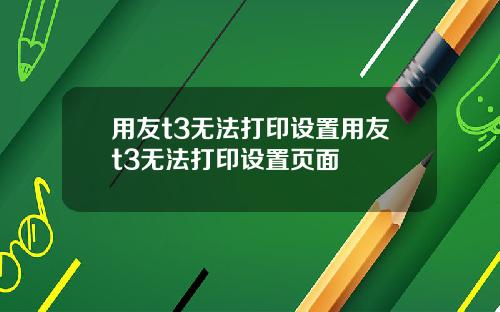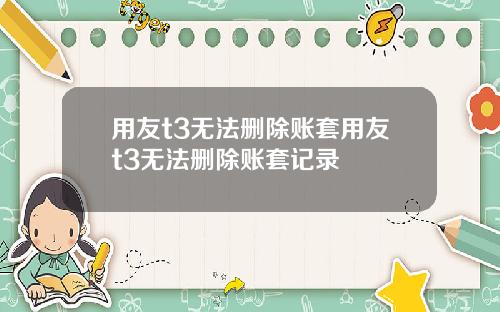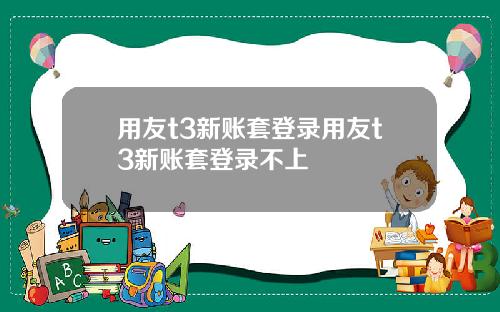光明网02-19 08:34显示图片
苦日子熬过来的,现在更没什么好吵的
本报记者彭洁
一杯桂花水
下午三点,天色阴沉,风凉凉地刮着,一副大雨欲落的样子。
张士友家的客厅兼书房,开着一盏白晃晃的台灯,狭小的房间有些昏暗。进门一侧的墙上,挂满装裱好的剪报,那是2008年以来各级媒体对他的报道——《张士友:66本日记本》、《老张日记五十年》、《张士友:日记本里的30年变迁》、《透过古戏把脉当下变迁》、《见证幸福的家庭档案》……
“你来这里坐,好写字。”张士友满脸笑意,眼睛眯起,眉间的皱纹拧成“川”字。把我招呼到书桌前,他转身在对面的沙发坐下,又对站在墙边的老伴说:“你快给记者倒杯烫的桂花糖水,今天外面可冷呢。”
王桂芳笑着应声,转身从柜子上拿下一个纸杯。她的头发稀疏,银色中夹着几根黑丝,整齐地盘在脑后,精神硬朗。
“这桂花是从家后面的桂花树上摘下来的,老太婆自己做的桂花糖,泡水喝又香又甜,很有味道。”张士友将掉在额前的几缕头发捋了捋,依旧笑着对我说。
低头一饮,唇齿留香,“阿婆,很好喝。”王桂芳也笑了,脸颊两边松弛的肌肉向上微微鼓起,面容慈祥,“那就多喝点吧!”
屋子里,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。
从不吵架
“我们1958年结婚的,到现在……57年了,从来没吵过架。”昏暗中,张士友低头想了想,算出时间后又马上抬起头。此时,王桂芳找了把椅子,在对面的墙边坐下,听到老伴儿喊出“57年”,也不由一笑,冲我摆摆手说:“没吵过,没什么好吵的,苦日子熬过来的,现在更没什么好吵的。”
那年,张士友22岁,王桂芳19岁,经人介绍后结了婚——从一张黄旧的结婚照上看,彼时,张士友面容俊朗、剑眉星目,唇角微微勾起;靠在他身前的王桂芳眉目清秀,乌黑的头发编成两股束在耳侧,一脸稚气。
张士友说:“我们在一起经历蛮多事情的。”他的语气缓慢平淡,几不可闻。
事实上,在大女儿珍出生之前,他们还有个儿子。只是,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之中,儿子7岁的年幼生命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河里戛然而止。丧子之痛让王桂芳深受打击,夜夜垂泪,丈夫张士友常常用臂膀倚住妻子,轻声安慰。
珍三岁时,大儿子红卫出生;又三年后,小儿子红坚出生。生活的艰辛迅速压了下来。
那个时候,家里的成员除了3个子女,还有张士友年迈的老母亲,一家六口的生计,主要靠张士友每月30元的工资支撑。王桂芳心疼丈夫,便趁着孩子睡觉、老人小憩的功夫,四处揽手工活贴补家用。
阴霾的光从阳台的纱窗晃进屋里,一下,一下,印着王桂芳的皓首苍颜,“那时候,真难。”她说。
刚结婚时,王桂芳狠心买了一件钟意已久的灯芯绒外套。女儿珍渐渐长大,这件衣服两侧的毛已被磨得精光,王桂芳不舍得扔,布厂工人出身的她寻了把剪刀,把外套改小,当新衣服穿到了珍的身上。又过几年,衣服磨损得愈发厉害,没了外套的样子,王桂芳拾过来,又改成一件马甲,穿在了红卫身上;又几年后,贴上几块布,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衣服,套在红坚身上……
日子,就这样在相濡以沫中过去。
专车接送去看戏
在2008年8月15日这天的日记中,张士友写道:“目前女婿家有4辆车,大儿子有私家车2辆,小儿子家2辆……”老人欣喜,家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更感欣慰的是子女的孝顺——女婿和儿子的车,几乎都做过同一件事情:接送张士友看戏。
1996年,张士友从干了近40年的路桥布厂厂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,却发现自己更忙了。“忙啊,忙着看戏。”他坐着,一拍大腿,大笑着说。
张士友喜欢看戏。他略微统计了一下,五年前,他先后去了199个村庄,看过344个省内外剧团的演出,每年看戏的场次基本在500场左右。
“我不光看戏,每次到剧院里看花了钱的戏,我会把戏票和剧照收起来,还拉演员合影,回到家,再把每一台戏看的时间地点、票价和感受都写下来。2008年那一年,我一共赶了187场庙会……”
张士友看戏的范围很广,从附近村落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杭州、上海,只要他知道哪里有戏,就会去看。“近的地方还好,那远处,您这么大年纪,怎么去?”我问道。
张士友“哈哈”一笑,“我儿子、女婿都开车送我去,再把我接回来!”有时候,为了让老爷子在杭州、上海能好好看场戏,儿子或女婿会开车载着他提前一天出发,陪着他住一晚,第二天戏看完了,再一同开着车回来。
“怎么样?就这份孝心……两个媳妇儿从来没抱怨过……我知足啦!”
这家人
张士友,80岁,路桥区路桥街道商城社区居民,退休前任路桥布厂厂长。妻子王桂芳,77岁,两人育有子女三人。
从1956年开始,张士友坚持写日记,至今已有59年。2009年,他将自己数十年来收集的生活资料——大约3万件藏品,整理后建成了台州市首个家庭档案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