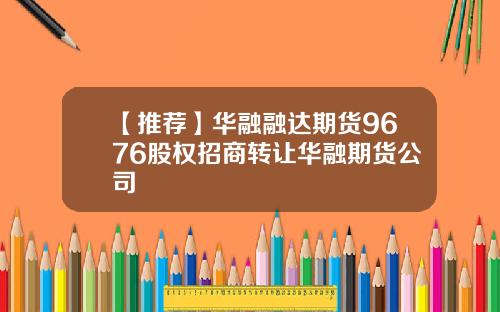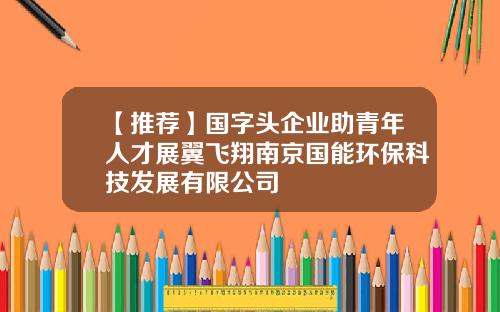太阳还在沉睡,海天混沌一色。海面轻轻泛起褶皱,像绸子上细碎的纹理。渐渐地,白色天光开启,一道暗痕卧于海天之间。海水的灰色绸子涌起厚重的波纹,一道一道,蛰伏在水底,接连涌动着,驱赶前浪,无休无止。
一道道波纹拍岸而来,凌空跃起,击碎在沙滩上。一片轻薄水雾扫过,海浪就暂停了它侵袭的步伐。它低吟着,退回海中,像一只昏昏沉睡的兽,在起起伏伏地呼吸。渐渐地,海天之间的那道暗痕明亮了起来,像酿酒时沉渣落定,古旧的绿色瓶身透出澄澈的光亮。这白色的沉淀落了下去,横亘在暗痕之后的天空就明朗了起来。天际之下,好似有一只妇人之臂,擎着一盏明灯,它的光线或白或绿或黄,如同辐辏,又四散开去,穿越天空。她把灯举得更高了,像一丛篝火,吐出红色黄色的纤状火舌,裹挟着烟雾咆哮而来,将一面碧水照得闪现出粼粼的光,好像也要燃起烈焰来;照得空气都现出了它的丝丝纹理,要与海水撕裂而去。这篝火的火舌渐渐汇聚成一团明亮而炽烈的迷雾;天空原本灰沉沉的,像覆盖了一层羊毛,此刻也变得轻盈起来,在这白光的映射下显现出无数柔和的蓝光点点。海面慢慢变得透亮,卧在天底下,泛起涟漪,闪闪发光,直至那道暗痕被抚摩消失殆尽。那只天际的妇人之臂将明灯徐徐举起,推向更高。宽阔的火舌消散,一团燎焰在海的边缘形成一道弧形的拱门,无垠的海水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
这光芒降临到花园里的树木上,把树叶照得片片透亮。鸟鸣间或,高低错落。太阳把屋子的墙壁照得更加分明。它悬在那里,像白色窗帘上半月型窗户的扇尖,抚过卧室窗前的枝叶,留下一片绿荫。窗叶轻轻碰撞,但屋内的一切都暗淡幽微,窗外响起不知所云的鸟鸣。
“我看见一个圆环,”伯纳德说,“悬在我眼前,微微颤动着,四周围绕着一个光圈。”
“我看见一抹厚重的暗黄色光影,”苏姗说,“蔓延着,和一道紫光相接。”
“我听见一个声音,”萝达说,“吱啾,吱啾,上下跳跃。”
“我看到一只球,”内维尔说,“在山坡巨大的侧翼下悬着。”
“我看到一根深红色的穗子,”珍妮说,“和金线缠绕一起。”
“我听到顿足的声音,”路易说,“一只巨兽被铁链拴住了脚,咚,咚,它原地跺着脚。”
“看那阳台角落里的蛛网,”伯纳德说,“挂着一串串水珠,滴滴闪着白光。”
“窗户周围散落的树叶像动物尖尖的耳朵,”苏姗说。
“影落道上,”路易说,“像人弯折的臂肘。”
“光影在草坪上游荡,星星点点如同岛屿,”萝达说,“它们从树叶的缝隙中渗漏下来。”
“树叶之间的狭长缝隙里,鸟儿的眼睛十分明亮,”内维尔说。
“花茎上覆盖着短小粗粝的绒毛,”珍妮说,“嵌着一些露珠。”
“一条毛虫蜷成一个绿色的环,”苏姗说,“长着平圆的短脚。”
“一粒灰壳蜗牛挪过小径,碾得身后的草叶平平的,”萝达说。
“窗户玻璃反射的炙热阳光,在草丛间穿来折去,”路易说。
“我的脚碰了碰石头,感觉它很凉,”内维尔说,“圆的、尖的石头,我一个一个的,都碰了它们一下。”
“我的手背火辣辣的,”珍妮说,“但手心却黏糊糊的,沾满了露珠。”
“尖厉的鸡鸣像白色潮水中一股硬硬的红色水流,迸发而出,”伯纳德说。
“鸟儿在我们身旁忽高忽低地穿梭,唱着歌,”苏姗说。
“巨兽在顿足,那是一只身体粗笨的大象。它的脚被链子拴了起来,在海滩上跺脚。”路易说。
“看那座房子,”珍妮说,“它所有的窗子都挂着白色的窗帘。”
“后厨的龙头里流出了冷水,”萝达说,“流进装着马鲛鱼的碗里。”
“墙上长着金色的裂缝,”伯纳德说,“树叶狭长的蓝影映在窗户下。”
“现在,康斯特布尔太太穿上了她厚厚的黑色长筒袜,”苏姗说。
“炊烟升起的时候,睡意就像一丝迷雾,从屋顶盘旋着飘远,”路易说。
“一开始,鸟儿齐唱,”萝达说,“但后厨洗碗间的门没有锁,它们就都飞走了,像农人播种时撒出去的一把种子。但仍有一只还在卧室的窗子上独自歌唱着。”
“小煮锅的锅底冒出了一串气泡,”珍妮说,“它们往上升起,越来越快,形成了一串银链。”
“现在比利用一把锯齿刀在刮鱼鳞了,把鳞片都刮到了一张木砧板上。”内维尔说。
“餐厅的窗子已经变成了深蓝色,”伯纳德说,“烟囱上的空气像水波一样浮动。”
“一只燕子立在避雷针的尖端,”苏姗说,“比蒂又把水桶砸到了厨房的石地砖上。”
“教堂的钟敲响了第一声,”路易说,“接着又敲响了第二声;一声,两声;一声,两声;一声,两声。”
“看这块白色桌布,挂在桌边,飘摇着,”萝达说。“桌上有一个个白瓷盘,印着银色的纹路。”
“突然有一只蜜蜂在我耳里嗡嗡作响,”内维尔说,“它在我耳边;它又飞走了。”
“我燃烧起来,颤抖起来,”珍妮说,“逃离这阳光,躲进阴影里。”
“现在他们都走了,”路易说,“进屋吃早饭去了,就剩我一个人,站在墙边的花丛里。现在还很早,离上课还有很长时间。绿叶深翠茂密,衬得一朵朵花小小的。花瓣色彩斑斓,它们的茎植根在下面黑色的洼地里。花儿们好像光影化成的鱼,在深绿色的水面上游动。我手拿一枝花茎——我觉得自己就是这花茎。我的根在地底下,穿过混有砖块的或干燥、或潮湿的土壤,穿过流淌着铅和银的叶脉,与世界的深处相连。我的浑身上下都是纤维,颤动着,抽搐着,土壤挤压着我的肋骨。我的眼睛是绿叶,虽然睁着但看不见东西。我是一个男孩,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,系着一条带蛇形铜扣的皮带;我的眼睛没有眼皮,就像尼罗河边沙漠里的狮身人面像。我看见女人们肩扛着红色大水罐朝河边走去,骆驼蹒跚前进,男人们都扎着头巾。踩踏声,颤抖声,动荡声环绕着我,我听见了。
“在这里,伯纳德,内维尔,珍妮和苏姗在用他们的捕虫网撇去花床表面的一层土壤,但萝达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花儿们点着头,他们将花上的蝴蝶都赶走,仿佛把世界的表层都筛了一边。他们的网子里装满了扑扇的翅膀。‘路易!路易!路易!’他们喊道,但看不到我,我在树篱的另一边。篱笆的叶子上只有一些细微的孔缝。哦,主啊,让他们过去吧。主啊,让他们把手帕铺在砾石上,把蝴蝶都放在上面吧,让他们数一数乌龟壳,还有那些橘红边翅膀的蛱蝶和白色大蝴蝶,但请不要让他们看到我。我站在树篱的阴影里,像一株紫杉木。我的头发就是叶子。我扎根在土壤的中央。我的身体是一株躯干。我按了按手中的花茎,一滴浓浆从它的孔眼中慢慢流了出来,越流越厚重。突然,一个粉色的东西从树篱的缝隙中闪过,一道目光从缝隙里瞟了过来,它窥见了我。我不过是个穿灰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。她找到了我,碰了我的颈后一下。她亲吻了我。我感受到一阵惶乱。”
“吃完早餐后,”珍妮说,“我跑起步来。我从篱笆的缝隙里看到叶子在动,想‘那是巢里的鸟’。我把树篱拨开了一点,朝外边看去,发现鸟窝空空如也,可叶子还在动。我害怕了。苏姗,萝达,还有内维尔在工具房里说话,我跑过了他们,边跑边哭,越跑越快。到底是什么,让树叶不停地晃动?是什么,如此触动我的心,让我的双腿奔跑不停?我冲到了这里,看见你像一丛灌木一样青绿,纹丝不动,眼神一直注视着一点。‘他死了吗?’我想,然后亲了你。我的心在粉色的裙子下剧烈地跳动,就像那些叶子,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让它跳,却无休无止。我闻到了天竺葵的气味,泥土堆的气味。我跳起舞来,我的身体像水的波纹一样舞动。我像一张光线织成的网,撒出去,整个笼罩在你身上;笼罩在你身上,我微微颤抖。”
“从篱笆的缝隙里,”苏姗说,“我看到她亲了他。我在弄花盆,抬头看了看,从篱笆的缝隙里,我看到她亲了他。我看到了他们,珍妮和路易在接吻。现在,我要把我的苦恼和悲痛用手帕包裹起来,要把它紧紧扎好,攒成一团。上课之前,我要独自去一趟山毛榉树林。我再不会坐在桌前算算术了,也不要坐在珍妮和路易的身边。我要将我万分的痛苦安放在榉树的根上,审视它,用我的指尖抚摸它。他们找不到我的。我要以坚果为食,在荆棘丛中凝神寻找鸟蛋。我的头发将沾满灰尘,变得湿漉漉,乱蓬蓬,然后我就要睡在树篱底下,喝沟渠里的水,死在那里。”
“苏姗从我们身边跑过,”伯纳德说。“她从工具房门前跑过,将一条手帕紧紧地攒成一个团。她没有哭,但她那美丽的眼睛却眯成一条缝,像猫起跳之前的眼睛。我应该跟着她前去看看,内维尔。我应该悄悄跟着她,随时可以靠近她,在她突然悲愤大哭,心想‘我孤独无助’时安慰她,但我也不乏好奇之心。
“她充满生趣地雀跃着走过草坪,装作无忧无虑的样子,似乎是为了不让我们发现她的悲伤。然后她来到一处洼地;她以为没人能看见她,开始奔跑起来,两手紧握成拳放在胸前。她的指甲嵌入那个手帕的小团里。她正在朝那片山毛榉树林跑去,企图摆脱太阳的光亮。她跑到树林边时,撒开了双臂,以游泳一般的姿态跃入了树林的阴影里。但她的眼睛还未能适应黑暗,被树根绊倒,重重地摔在了上面。阳光微弱,时有时无,像人断续的喘息;树的交柯乱叶剧烈地起伏摇晃。她似乎很忧愁,被什么问题深深地困扰着。空气中愁云密布,光线游离不定,苦恼的汁液在蔓延。树的根茎在地上形成了一具骨架的形状,枯叶在它的曲折处堆积。苏姗掏出了她的悲痛。她的手帕躺在几棵榉树的根茎上,她啜泣着,蜷缩在刚才摔倒的地方。”
“我看到她亲了他,”苏姗说,“我从树叶的缝隙里看到的。她跳起舞来,树叶筛落的光斑掉在了她的身上,泛着细小的钻石光。而我却很臃肿,伯纳德,我很矮,站在地上,我都能看清草地里的昆虫。当我看到珍妮亲吻路易时,我胸中一团馨黄色的温暖瞬间变成了石头。我应该以青草为食,死于沟渠之中,死于枯枝朽叶堆积的一滩褐水里。”
“我看见你路过了,”伯纳德说,“你跑过工具房的门口,我听到你喊‘我不高兴了’。于是我放下刀——当时我正和内维尔一起拿柴火做一艘小船。我的头发乱糟糟的,因为康斯特布尔太太叫我去梳头的时候,蛛网里正有一只苍蝇被困在那里,我问,‘我能去看看那苍蝇吗?我要让它被蜘蛛吃掉吗?’所以我的行动总是慢别人一步。我没有梳头,头发里还缠着些木屑。我听到你在哭,就跟在你身后,看到你把手帕平铺着,又系成一个结,把愤怒和仇恨都打在了结里。但你过不久就会平息下来的。我们此时已经离得很近了,你听到了我的呼吸声。你看到甲壳虫背走了一片叶子。它一会儿往这边跑,一会儿往那边跑;你此刻看着这只甲壳虫,对路易那充满执念的欲望也开始动摇了,就像榉树枝条中里外游走的光线一样;随后,在你的脑海深处,言语隐晦地闪过,它们会解开系在这手帕中的苦涩之结。”
“我会爱,”苏姗说,“我也会恨。我只想要一件东西。我的目光是冷硬的。珍妮的眼睛里可以散发出千道光芒,萝达的眼睛像那些蛾子夜宿的白色花朵。你的眼睛呢,永远饱满,永远在闪耀,从来没有消散的那一刻。但我已经出发上路,开始追寻了。我可以看到草地里的昆虫。虽然妈妈仍给我织白袜子,缝围涎的边——我还是个孩子,但我知爱懂恨。”
“当我们坐在一起说话时,我们挨得很近,”伯纳德说,“我们说的这些话将我们融为一体。我们之间的边缘是一层薄雾,共同形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领域。”
“我看到了甲壳虫,”苏姗说,“它是黑色的,我看到了;是绿色的,我看到了;我现在好像只能说这么简短的字眼了。但你的思路会飘远;溜走;升得更高,不绝地说着一个又一个短句。”
“现在,”伯纳德说,“让我们开始探索游玩吧。树林间有一座白色的大房子,它静静地躺在我们脚下遥远的地方。我们要像游泳一样,让身体沉下去,踮起脚尖走在地上。我们要从这一片绿荫中沉下去,苏姗。我们一边下沉,一边奔跑,空气涌动成浪,拍过我们的头顶,榉树的叶子在上空交接。马厩里,时钟镀金的指针闪耀着光芒,大房子屋顶上一块凸起,一块平坦,小马倌儿穿着橡胶靴走在院子里哒哒响。这里就是埃弗顿。
“现在我们穿过树梢掉到了地上。空气冗长又乏味的紫色波浪原本卷过我们的头顶,现在也停歇下来了。我们摸摸土壤,脚站在地上。那一处就是小姐们的花园里修剪得整饬的树篱。她们在午时出来散步,手里拿着剪刀,剪下几朵玫瑰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片环形的树林,树林外围着墙。这里就是埃弗顿了。我在十字路口看见过指示牌,它上面写着‘通往埃弗顿’。但没人去过那里。羊齿植物气味浓烈,红色的蘑菇生长在它的下面。让我们叫醒这片林子里沉睡的寒鸦,它们从来没有见过人长得什么样子;让我们踩一踩这些腐烂的栎树瘿,它们红红的,看起来苍老又油滑。这林子外还围着一道墙,没有人会来到这里。听!这就是矮树丛里一只大蟾蜍扑通坠地的声音,这就是原生林中的松果掉落到羊齿植物中滴滴答答的声音,它们会腐烂在那里。
“你站在这块砖头上,看看墙的那边。那就是埃弗顿了。一位淑女坐在两扇长长的窗户之间写信。园丁拿着大扫帚扫草坪。我们俩是最先来到这里的人。我们发现了一片不为外界所知的土地。不要打扰他们;要是园丁发现了我们会开枪射死我们的。到时候,我们肯定无路可逃,像白鼬一样被钉在马场的门上。看!别动。抓牢墙顶的蕨类植物。”
“我看到那位写信的女士了,也看到扫草坪的园丁了,”苏姗说,“如果死在这儿,没有人会将我们埋葬。”
“跑!”伯纳德说,“跑!那个留着黑胡子的园丁发现我们了!我们会被他射死的!我们会像松鸦一样被射死,然后被钉在墙上!这一带的乡下对外人充满了敌意,我们得逃到榉树丛里去,躲在树底下。我来的时候折了一根细树枝作记号,那儿有一条秘密的小道。你弯下腰,越低越好。跟着我跑,别回头。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两只狐狸。快跑!
“现在我们安全了。现在我们可以重新站直身体了,在这榉树形成的广阔天蓬下伸个懒腰。我什么声响都听不见,唯有空中气流起伏的沉吟。那儿有只斑尾林鸽,把树蓬的天顶钻了个洞。它在空中扑扇,用它笨重的翅膀拍打着空气。”
“现在你的思绪又游离走了,”苏姗说,“造了一些漂亮的句子。你的思绪像一根气球底下的细线,往上升,拨开一层一层的叶子,越升越高,直升到我够不着的地方。一会儿你的脑袋又落后了,从后面拉我的裙子;往后瞧瞧,造了些漂亮的词藻。你从我身边逃走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花园和树篱前,萝达在小径上摇晃她褐色盆中的花瓣。”
“我的小船都是白色的,”萝达说,“我不要蜀葵和天竺葵的红色花瓣。把盆子略微倾斜,白色花瓣就会浮起来,那就是我要的。现在我有一艘游艇了,它从此岸驶向彼岸。我还要往里扔一根细枝,给那些落水的水手们当筏子。我要往里扔一块石头,看气泡从海底升起。内维尔走了,苏姗也走了,珍妮或许和路易在菜园里摘醋栗,哈德森小姐在课桌上发放我们的抄写本;我得以拥有一段独处的时光,我得以拥有一小块自由的空间。我把所有凋落的花瓣都捡了起来,放在水里让它们游泳,还在有些里面滴了些雨滴。我要在这里放一座灯塔,一座‘甜美爱丽丝’的头像。我把褐色水盆左右摇晃,这样小船们就可以踏着浪花前行了。它们有些进水、沉了下去,有些一头撞到了悬崖上;仍有一艘小船依然独自航行,那就是我的船。它驶进了冰窟,北极熊在里面咆哮,钟乳石挂着绿色的摇晃的链子。海浪越发汹涌了;它们卷起浪尖;看那桅头亮的灯,摇曳不定;它们沉沦了,所有的船都沉沦了,唯剩我的船依然在前行。它乘风破浪,来到鹦哥絮语、长着爬山虎的岛屿上。”
“伯纳德在哪里?”内维尔问,“他拿走了我的刀。当时我们正在工具棚里造小船,苏姗跑过门去,伯纳德就扔下了他的船,拿着我的刀追随苏姗而去了。那是一把尖刀,用来凿船龙骨的。他像一根悬挂着的缆绳,左摇右晃;像一只拉铃手柄,发出叮玲的响声。他像挂在窗外的海藻,一会儿干枯、一会儿湿润;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我而去,跑去跟苏姗去了;如果苏姗哭了,他会拿着我的刀跟她讲故事。簇新的大刀像个趾高气昂的皇帝,而卷了边的刀就像一个畏手畏脚的人。我讨厌晃荡的东西。我讨厌东跑西晃,把事情都搅和在一块儿。铃响了,我们都要迟到了。我们得放下手中的玩具,一块儿去上课了。我们的抄写本正一个个躺在绿粗呢台面的桌子上呢。”
“我不会主动说出这个动词的变位的,”路易说,“除非伯纳德先说。我爸爸是布里斯班的一位银行家,所以我说话有澳大利亚口音。我要等他先说,他是英格兰人。他们都是英格兰人。苏姗的爸爸是个教士,萝达没有爸爸,伯纳德和内维尔都是绅士的儿子,珍妮在伦敦和她的奶奶住一块儿。他们一会儿吮吸着笔,一会儿拧着抄写本,侧过身看看哈德森小姐,数一数她束胸上衣的紫色扣子。伯纳德的头发上还有块木屑,苏姗的眼睛红红的。两个人脸都红了。但我脸色苍白,衣着干净,灯笼裤上系着一条皮带,上面有只铜做的蛇。我心里对功课一清二楚。我知道的远比他们想象得多。我知道怎样给词变格,变性;如果想,我可以知道世上的每一件事。但我不想说出答案,让自己出类拔萃。我的根迂回复杂,像花盆中的纤维,一圈一圈地围绕着世界打转。我不想出人头地,像这黄色板面的大钟一样活着,一刻不停地滴答,滴答。珍妮和苏姗,还有伯纳德和内维尔,他们几个合起伙来,变成一根皮鞭来抽打我。他们嘲笑我衣着整洁,我的澳大利亚口音。不过现在,我就要来模仿伯纳德那软绵绵、‘s’‘th’不分的拉丁语口音了。”
“这些是洁白的词,”苏姗说,“在海边捡的石头那种颜色。”
“我们说这些词的时候,它们的尾巴就左右摇来摇去,”伯纳德说,“它们摆动着尾巴,它们轻弹着尾巴;一会儿朝这边,一会儿朝那边,一齐动,一会儿分开,一会儿又聚拢。”
“这些是黄澄澄的词,那些是火焰一般橙红色的词,”珍妮说,“我想要一条火焰颜色的连衣裙,一条黄色的连衣裙,一条茶色的裙子晚上穿。”
“每一个时态,”内维尔说,“都有不同的含义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秩序的,但世界也有区别,有差异。我现在踏上了这世界的边缘,因为这只是个开端。”
“哈德森小姐,”萝达说,“已经合上了书本。可怕的时刻到来了。她拿起一根粉笔头,在黑板上画起一些图形来,六个,七个,八个,还有一个十字,一条线。此题怎解?大家都看着她画,都懂了她的意思。路易开始写起解答过程来;苏姗也写起来;内维尔写起来;珍妮也写起来;就连伯纳德都已经开始做题了。可我不会。在我眼里,它们只是图形而已。大家挨个上交了答卷,现在轮到我了,可我没有答案可交。大家都可以下课了。他们关上了教室的门。哈德森小姐也已经走了,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解题。但我看不懂这些图形,它们的意义仿佛已经消失。时钟发出滴答的响声,它的两条指针是在大漠中跋涉的车队,钟面上的黑色条纹就是绿洲。分针向前奔走着寻找水源,而时针只能痛苦地在沙漠炙热的石块中跌跌撞撞,它就要死在沙漠里了。厨房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。远处传来野狗的吠声。看,黑板上那些图案中的圆形开始被时间填满;它把世界圈了进去,而我却在这个圆圈之外。我现在要开始画一个圆——像这样——好了,一个闭合的圆。世界自成一体,可我却在它之外,大喊着,‘哦,救救我,我被永远地驱逐到光阴之圈的外面了。’”
“萝达坐在那里,盯着黑板,”路易说,“她坐在教室里,而我们在郊外悠闲地散步,这里摘一点百里香,那里捡一片青蒿的叶子,听伯纳德给我们讲个故事。萝达的两块肩胛骨在背后碰到了一块儿,像小蝴蝶的翅膀。当她盯着那些粉笔画的图形看时,她的思绪仿佛就寄宿到了那些白色的圆圈中去,独自跨过它的边界,迈入其中的空无中去。这些图像对她来说毫无意义,她也不知道如何解答。她不像其他人那样,她没有身躯。而我呢,说着澳大利亚口音,爸爸是位布里斯班的银行家,对她也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的惧怕。”
“让我们从醋栗树枝叶形成的棚顶下,”伯纳德说,“慢慢地爬过去,讲故事。让我们去那底下的世界安家,营造一片不为外人道的地盘。悬垂的醋栗树枝就像一个大烛台,照亮着我们,一侧闪着红光,一侧还是黑漆漆的。珍妮,如果我们再坐近点,就可以坐在醋栗树的天蓬下,看那些香炉来回摇曳。这就是我们的世界。其他人乘着马车路过。哈德森小姐和嘉丽小姐的裙摆像烛熄一样扫过。苏姗穿着白袜子,路易干干净净的沙滩鞋用力地踩在碎石头上。阵阵暖风带来腐烂叶子和植被的气味。我们现在在一片沼泽里,在一片疟疾肆虐的丛林里。一头大象被箭射中眼睛而死,身上覆满了白色的蛆虫。老鹰,秃鹫在周围跳动,眼神明亮,也是可以想见的。它们把我们当成了倒下的树。它们去啄一条虫子——却发现是条戴头巾的眼镜蛇——给它留下了一道棕色的溃烂的伤痕,只待狮子去凌虐。这就是我们的世界,新月和星光将它照耀;半透明的花瓣拥在它的入口,像一扇扇紫色的窗户。每样事物都非常奇怪,不是特别庞大就是特别微小。花茎有橡树那么粗,树木像教堂宏伟的穹顶那样高。我们都是巨人,躺在这儿,森林会因为我们而颤抖。”
“也只有此时此地是这样,”珍妮说,“但我们一会儿就要走了。不一会儿,嘉丽小姐就要吹哨子了。我们此刻对谈,随后分开。你们要去学校上学。你们的男老师都戴十字架,系白领带。而我会去东海岸的一所学校,有一位女教师,她坐在亚历山德拉王后[1]的画像下。这就是我要去上学的地方,还有苏姗和萝达。我们此刻憨顽的情景以后再不会有了。我们躺在醋栗树下,每次微风徐来,斑驳的树影就掉落到我们全身,让我的手看起来像蛇皮一样,一片一片的,膝盖上有一座座漂浮的粉色岛屿。你的脸就像一棵苹果树,底下张着打苹果用的网。”
“热气就要消散了,”伯纳德说,“从林子里消散了。树叶黑色的翅膀在我们头顶扑扇。嘉丽小姐已经在台上吹响了她的哨子。我们必须得从醋栗树的凉棚里爬出来、站起来了。你的头发里有几根细小的树枝,珍妮,你的脖子上爬着一条绿色的毛虫。我们必须两个一排站好队,哈德森小姐坐在她的书桌前登记我们的成绩时,嘉丽小姐要带我们去轻快地散散步。”
“这可真乏味,”珍妮说,“就这么走在大街上,又没有房子的窗户可看,也不能透过它们朦胧眼睛一般的蓝色玻璃,望见里面的过道。”
“我们必须两个两个站好队,”苏姗说,“踏着整齐的步伐,不能拖拖拉拉,不能落后掉队。路易走在前面引导着我们,他人很机灵,不容易走神。”
“因为我身体太弱,”内维尔说,“一不小心就会疲累患病,所以不能和他们一起去了。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不必和人攀谈,我便可以从独处中获得缓释,围着房子的边缘散散步。如果可以的话,我还要站在楼梯平台往上半道的一级台阶上,恢复一下昨天厨子猛烈地推拉火炉的风门,我从弹簧门那儿听到他们谈论那死人时的感受。别人发现他时,他已经被割了喉咙。苹果树的叶子在空中戛然静止;月亮对人间怒目而视;我也没有力气拔起脚来,继续上楼。他是在一个水沟里被人发现的,他的血汩汩地流到了沟里,面颊像死鳕鱼一样惨白。我要永远地把这残忍无情的事故叫做‘苹果树丛中的惨死’。天空中飘过浅灰色的云,树木萧异诡谲,树皮都戴着托叶鞘,闪着银光。我的生命中泛起的波纹都是徒劳的。我无法度过它。这里有一道障碍。我说,‘我无法越过这道晦涩难懂的障碍。’其他人纷纷从旁边走过,但我们所有人都在劫难逃,难以逃脱那些苹果树,那些狰狞的凶恶的树林。
“现在,惨烈、无情的情绪已经过了。下午靠近傍晚时分,落日在地毡上撒下一个个油亮的小光斑,日影斜斜地照在墙上,让椅子的腿看起来像断了一般,此刻,我就要继续探索房子的周围了。”
“我在厨房里看到弗洛莉了,”苏姗说,“我们散步回来,看见洗完晾晒着的衣服在她周围被风吹得鼓鼓作响,睡衣,衬裤,还有睡袍,都急急地迎着风。欧内斯特亲了她。他穿着绿粗呢围裙,正在擦拭银器;他吸着嘴巴,直让它像个起了褶子的钱夹。隔着他们俩中间挂着的、在风中剧烈鼓动的睡衣,他紧紧地抓住她,像一头公牛一样盲目。她难受得快晕了过去,惨白的脸上布满一根根细小的红血丝。下午茶时间,他们递来一碟碟面包和黄油、一杯杯牛奶,但我却看到地上裂了一条缝,一缕热气咝咝作响从地里冒出来,大茶壶也发出咆哮的声音,像欧内斯特那样。我轻轻咬了一口涂了黄油的松软面包,舔了一口甜牛奶,但此刻我却感觉自己就像那件睡袍一样,在风中剧烈地鼓动。我既不怕酷暑,也不畏寒冬。萝达好像在做梦,她把一块泡在牛奶中的面包皮吸到了嘴里;路易用他蜗牛一般的绿色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;伯纳德把他的面包揉成一个个小球,说他们是‘小人儿’。内维尔已经以他一贯利落果决的姿态把面包给吃完了。他卷起了餐巾,套进了餐巾环里。珍妮拿她的手指在桌布上画圈,好像在阳光下旋转着舞动。但我不惧酷热与寒冬。”
“现在,”路易说,“我都起来吧,我们都站起来。嘉丽小姐已经把她的记错簿摊开放在小风琴上。每当我们歌唱、睡觉前向上帝祈祷保佑我们平安、叫自己小孩子的时候,都难以抑制住哭泣的冲动。当我们因为内心忧郁不安而颤抖的时候,一齐歌唱能让我们感受到亲密的慰藉。我们的身体要稍稍倾斜,我朝苏姗轻轻倾斜,苏姗朝着伯纳德;我们的手要紧紧相握,心中充满了害怕——我害怕自己的口音,萝达害怕图形;但我们都非常坚定地要战胜我们的恐惧。”
“我们像小马驹一样结队上楼,”伯纳德说,“登登地踏着楼梯,争先恐后地上楼去洗澡。我们推搡、扭打成一团,在白色的硬床上上窜下跳。轮到我了,现在我要去洗澡了。
“康斯特布尔太太腰间系着浴巾,拿着她柠檬黄的海绵;海绵一浸在水里,就变成了巧克力一样的褐色;海绵滴着水,她把它高高地举过我的头顶,我在她身下瑟瑟发抖;她于是挤了一下海绵,水就沿着我脊背的沟壑流了下来,两侧感到一阵酥麻,像被闪着光亮的箭头射中了一样。我浑身的皮肉都暖和了起来,干涸的缝隙得到浸润,冰冷的身体变得温暖。水冲刷着身体,令它闪闪发光,从上面流下来,包裹着我,像包裹着一条鳝鱼。现在,一条热热的浴巾将我卷了起来。我用它擦背,那粗糙的摩擦感让我的血液发出咕噜咕噜的流淌声。我的脑际充盈着浓厚的兴致;一天之内的际遇都随着水一起流下——森林;埃弗顿;苏姗和鸽子。他们像水一般沿着我脑海中的墙壁倾泻而下,汇聚在一起。这一天丰富又冗长,光辉绚烂。我松松地系上了睡衣,躺在被单下。被单漂浮在浅色的光线中,像海浪卷来的一层薄薄的水膜,笼罩在我眼前。在浪声里,我远远地听到了极远极弱的一种声音,是合唱团开始歌唱了;车轮声;狗吠声;男人的呼喊声;教堂的钟声;合唱团开始唱歌了。”
“我叠起了衬衣和连衣裙,”萝达说,“我已经不再渴望成为苏姗或者珍妮了,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。我要张开脚趾,碰到床尾的围栏;触到它,我会有一种确信感,因为那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。现在我不能沉沦,不能全然放纵自己从这薄薄的被单里坠落。我在这岌岌可危的床垫上摊开身体,仿佛悬躺在空气中。我现在就在大地之上了。我的身体不再是直立的,也就无法被击倒,或受到伤害了。一切都柔软而圆融。墙和壁橱好像被漂白了一般,它们方方的柜角变圆了,顶上一面镜子发出暗淡的光。现在,我的思绪可以恣意流淌了。我可以想象我的无敌舰队在高昂的海浪上乘风破浪,不曾与别的船发生摩擦或碰撞。我独自从白色的悬崖下驶过。哦,但我还是沉没了,坠落了!那是壁橱的柜角,那是托儿所的穿衣镜。但是它们伸展了,延长了。睡意像一团黑色的羽毛,我沦陷在其中了;它厚厚的翅膀逼进了我的眼睛。我在黑暗中游历,看到花床也延伸开来,康斯特布尔太太从一块蒲苇丛的角落后面跑出来,说小姨坐着马车来接我了。我跑上楼;我逃跑了;我蹬着弹簧靴跳过了树梢。但现在我还是坠落到了堂前的马车里,小姨坐在里面,她摇着黄色的羽毛扇,眼神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冷硬。哦,快从梦中醒过来吧!看,这是一个抽屉柜。让我从这一片浪涛中把自己拽出来吧。它们向我扑来;它们巨大的肩膀裹挟着我,把我卷得颠三倒四,翻滚、跌倒;在这狭长的光线里,绵延的海浪中,无尽的道路上,我延展开来,人群在追寻,在追寻。”
[1] 亚历山德拉王后(Queen Alexandra),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妻子(1844-1925)。(译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