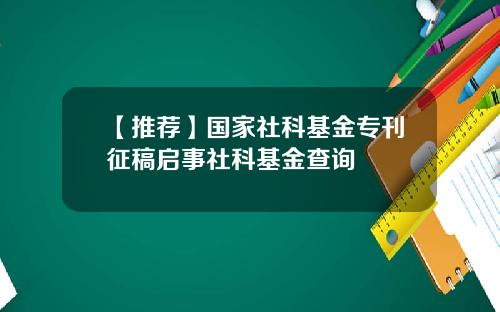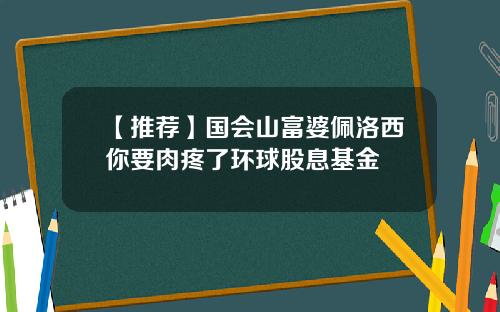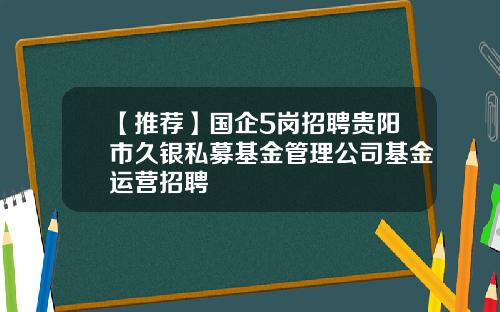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20年第44期,原文标题《儋州:兹游奇绝冠平生》,严禁私自转载,侵权必究
儋州三年,为东坡最后谪居之所。在宋人眼中的畏途上,东坡继续着自己对于人生与政治的思索,完成了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《书传》等重要学术著作。一如既往地,他仍然感受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乐趣,留给后人说之不尽的“笠屐图”。
记者/艾江涛
摄影/刘有志
儋州市仁和镇东坡书院,前身是东坡好友黎子云家的载酒堂,东坡曾在那给当地学生讲学,元代后这里曾建东坡祠
岭海间的诀别
绍圣四年(1097)六月十一日清晨,苏轼从广西徐闻一个叫递角场的地方,与弟弟苏辙挥泪诀别,然后登舟渡海,前往儋州。两个月前,苏轼在惠州贬所刚建好自己的白鹤新居,长子苏迈全家和幼子苏过的家眷,经过一年多长途跋涉也到了惠州。就在苏轼正准备和家人一起在这里安度晚年时,朝廷一纸诏令下来,责授他琼州别驾,昌化军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
“军”在宋代是一个以军事为重的行政建制,主要用于沿海、沿边和前线。北宋末年,海南省的建制为一州三军。一州,即所谓琼州,北宋熙丰年间,朝廷在琼州设“琼管安抚司”,主管全岛军政事务,为海南最高行政首府,治所在今天海口的琼山区。三军,即为西边的昌化军,南边的吉阳军,东边的万安军。由于苏轼被任命为琼州别驾,昌化军安置,意味着他首先要到琼州府衙报到,然后再去今天位于儋州市仁和镇的昌化军治所安置。
这一年四月十九日,62岁的苏轼在惠州作别家人时,意识到自己“垂老投荒,无复生还之望”,为此立下遗嘱,并对长子苏迈吩咐了后事,便带着25岁的幼子苏过出发了。走到梧州时,得知弟弟苏辙被贬到雷州,兄弟俩便相约在藤州相会,一起赶赴雷州。到雷州后,苏辙将哥哥一直送到海边,才依依惜别。
本来到黄州之后,苏轼境遇好转。尤其是神宗皇帝在元丰八年(1085)去世之后,他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,旧党得到大量起用,苏轼得到火箭式提升,几年内就从秘书省校书郎一路升迁到门下侍郎(副宰相),一度担任年轻的哲宗皇帝的老师。但随着高太后在元祐八年(1093)去世,已经亲政的哲宗皇帝带着对祖母的强烈不满,次年改年号“绍圣”,意谓继承神宗朝的政策方针,苏轼等人被再度贬谪的命运已经注定。
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报复行动来得如此猛烈。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,定州知州任上的苏轼,接到第一道谪命:取消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,撤销定州知州,以左朝奉郎知英州(治所在广东英德)军州事。就任途中,朝廷四改谪命,一直将他贬为建昌军司马,惠州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转眼之间,苏轼又成了没有公务的贬官。
只是,有了黄州时期的历练,此时的苏轼再也没有过去的彷徨痛苦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告诉我,他登上大庾岭后,才明白了《过大庾岭》这首诗。“苏轼被贬惠州,从江西吉安到广东韶关过梅关,在大庾岭上写了一首诗,其中两句‘浩然天地间,唯我独也正’,把他面对贬谪的心态说得特别清楚。这两句话是庄子讲的,‘受命于地,唯松柏独也正,在冬夏青青;受命于天,唯尧舜独也正,在万物之首’。他那种自信的人格展露无遗。再者,他相信自己能回得来,所以接着写‘仙人抚我顶,结发授长生’。”
在黄州时期形成的“不在其位也谋其政”的思想,让苏轼一到惠州,又继续为百姓做起了实事。他建言州县官员添建营房、整肃军政;督促官员救援台风、火灾等灾情;而且还促成了惠州东西二桥与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。
此番到了海南,一个远离大陆的穷苦孤岛,已经贬无再贬。据说,苏轼在惠州写了一首《纵笔》:“白头萧散满霜风,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政敌章惇看后觉得他日子过得太舒服,继续把他贬到海南儋州。
苏轼在海南究竟在哪登陆,到底在澄迈还是当时琼州府的治所琼山?历来都有争议。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会长李公羽告诉我,他专门就此写过考证文章:“海南西线历来受风浪影响比较小,从唐到南宋,从大陆广西徐闻渡海而来,一直都在澄迈的港口登陆,南宋以后海口才有港口。”
东坡当年刚到海南,曾在琼州府官驿逗留十多天,以“琼州别驾”的虚衔,他不愿与当时的琼管安抚司长官张景温见面,上书声称“知舟御在此,以病不果上谒”。不过,他并没有闲着,在今天海口五公祠内,仍留有一口称为“浮粟泉”的井,据说正是东坡看到当地居民饮用不干净的水源,指地让人发掘而成。之后,东坡沿着海岛西路线,取道澄迈、临高,于七月二日,抵达贬所昌化军治所儋州。
海南的天气忽而大雨忽而烈日,阴晴无定,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在海口老城仍留存一条骑楼老街。所谓骑楼,是一种从南洋流传而来的受到欧洲建筑风格影响的外廊式建筑,主要目的便是应对海南强晒多雨的气候,起到遮雨防晒的作用。东坡当年在从琼山到儋州的路上,便遭遇了狂风急雨的天气,这或许是海岛留给他的第一印象:“四州环一岛,百洞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,如度月半弓。登高望中原,但见积水空,此生当安归?四顾真途穷!眇观大瀛海,坐咏谈天翁。茫茫太仓中,一米谁雌雄。幽怀忽破散,永啸来天风。千山动鳞甲,万谷酣笙钟。安知非群仙,钧天宴未终。喜我归有期,举酒属青童。急雨岂无意,催诗走群龙。梦云忽变色,笑电亦改容。应怪东坡老,颜衰语徒工。久矣此妙声,不闻蓬莱宫。”群山环抱、海波浩渺,疾风骤雨的旅途中,苏轼考虑的仍是能否北归的问题。
海口五公祠中的浮粟泉,据说是绍圣四年(1097)七月,东坡初到琼州府看到当地居民饮用不干净的水源
海岛上的乐趣
到达儋州贬所,苏轼和儿子暂时在几间租借的破旧官舍栖身。旅途中陌生的兴奋感很快消散,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气候难以适应、物资极度匮乏的陌生处境。
海南湿热多瘴气,历来被中原人士视为畏途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,韦执谊当宰相时,在相府中看地图,每看到崖州时则闭目不观,恶其瘴毒,到者必死。
在写给朋友的信中,苏轼如此描述当地的穷乏:“此间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,然亦未易悉数,大率皆无耳。”一句话,在儋州的新生活,几乎是要什么没什么。
好在八月间,新任昌化军军使张中就任。途中,张中遇到雷州知州张逢,后者是东坡门生,从他那里,张中对这位令人景仰的大文豪有了更多了解。带着张逢写给东坡的书信,一到儋州,张中便去拜访苏轼,并派人整修官舍,改善苏轼父子的住宿条件。不仅如此,张中还经常邀请苏轼父子到府衙下棋喝茶,一解寂寞苦闷的生活。
如今的儋州仁和镇,依然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古镇,并不宽敞的街道两边遍植棕榈,店铺林立。在据说是当年府衙所在地的镇政府院中,如今还树有苏轼所写的《观棋》那首诗的纪念牌。“长松荫庭,风日清美。我时独游,不逢一士。谁欤棋者,户外屦二。不闻人声,时闻落子。纹枰坐对,谁究此味。空钩意钓,岂在鲂鲤。小儿近道,剥啄信指。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。优哉游哉,聊复尔耳。”一幅悠然惬意的景象。
喜欢交游的苏轼,不久便结识当地大户黎子云兄弟。黎氏兄弟虽务农为业,但家境殷实,常常邀请张中和苏轼一起到家中饮酒游乐。黎子云有次新建了一座房子,请东坡命名,东坡取意《汉书·杨雄传》中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,起名“载酒堂”,并在这里为当地学生讲课。这里正是如今在仁和镇所能看到的东坡书院的前身,到了元代这里建起东坡祠,明清时又成为书院。现在的东坡书院俨然成为仁和镇的著名景点,虽然这里除了一块元代石碑,便无其他更早的遗迹,但园中古木葱郁,亭台井然,成为东坡迷们的必到之所。
在海南期间,我曾和朋友一起环岛骑行,骑至儋州境内,发现每过一村,几乎都能看到村口搭建的祝贺当地学生高考得中的对联彩棚。李公羽告诉我,儋州不少村落文风很盛,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能根据情境现拟对联,平仄韵律无不妥帖。或许,这正是东坡在海南千载以来的影响所至。东坡去世以后,曾在儋州追随他学习的琼州人姜唐佐高中进士,成为海南历史上首位进士。
就在苏东坡逐渐适应当地生活时,新党对他的迫害并没停止。章惇命令湖南监察御史董必到儋州监察,看当地政府有无破格接待苏轼。途中,一名叫彭子民的随员流泪劝说董必:“人人都有子孙。”良心发现的董必,改派小使过海察看,最终还是把苏轼父子逐出官舍。张中带领当地百姓和苏轼的学生,很快在一片桄榔林中为苏轼搭建起新居。桄榔庵落成后,兴奋不已的苏轼还作诗《新居》:“朝阳入北林,竹树散疏影。短篱寻丈间,寄我无穷境。旧居无一席,逐客犹遭屏。结茅得兹地,翳翳村巷永。数朝风雨凉,畦菊发新颖。俯仰可卒岁,何必谋二顷。”
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文德路上的餐馆
如今的桄榔庵,淹没在一块菜地中,除了门口的保护牌及园中一块明代复建时的石碑外,别无他物,更连一棵桄榔树也没有。当地村民告诉我,桄榔不如槟榔、椰子经济价值高,故多不种。但距此不到两百米的东坡井,确系东坡当年带人开凿,居住桄榔庵期间的饮用之水都从此来。这口古井经过多次修缮,旁边还有一块清道光年间重修的碑刻,井口不但石沿齐整,而且外围建了水泥围栏,井水深幽清亮。村民告诉我们,五年之前,在自来水管道铺设前,当地人还在饮用井水。我们从村民家借来水桶,打水喝了一口,口感清甜。
就是在这里,东坡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贬谪时光。那时的他,究竟过得如何?从他留下的诗文来看,东坡的儋州岁月依然充满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乐趣。
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书信《献蚝帖》中可以看到,苏轼找到吃生蚝的乐趣,不但讲述了制作方法,还告诉朋友,“每戒过子慎勿说,恐北方君子闻之,争欲为东坡所为,求谪海南,分我此美也”。一派老顽童的样子。
“明日东家知祀灶,只鸡斗酒定膰吾”的诗句写出寒食节前夕,苏轼对邻居杀鸡请酒的期待。“小儿误喜朱颜在,一笑那知是酒红”是一幅醉翁与儿童的嬉戏图。“半醒半醉问诸黎,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,家在牛栏西复西。”则描述苏轼醉后迷路,黎子云家的孩子告诉他:顺着牛屎走就能找到。
如果说竹杖芒鞋,是东坡在黄州时期的经典造型,那么在儋州,他的经典造型便是“笠屐图”。多种宋人笔记都记载了这一故事:东坡有次去黎子云家途中遇雨,便从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穿上。妇女儿童见状一路笑随,就连一旁的狗也叫起来,似乎都在讶异眼前这位大学士滑稽的装束。
历代文人画家钟情于东坡笠屐的故事,创作了大量的东坡笠屐图。据考证,现存笠屐图共有150多个版本。在这些版本中,李公麟的《东坡笠屐图》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作品,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人朱之蕃临李公麟的《东坡笠屐图》,接受度无疑最广。这幅图卷上,东坡戴着宽大的海南斗笠,面部丰腴,长须下垂,双手提着衣襟,穿着木屐在雨中赶路的景象跃然纸上。南宋赵孟坚与明人仇英的《东坡笠屐图》中,东坡手中还拿有一根竹杖,似乎是竹杖芒鞋与笠屐图的某种结合。元人赵孟頫的《苏文忠公笠屐图》中,东坡则左手掖着衣襟,右手背后,神态淡然,似乎并无泥泞中赶路的窘态。
儋州市中和镇宁济庙,苏东坡贬谪儋州,曾前往这里拜谒,并留下“庙貌空复存,碑板漫无辞”的诗句
天不丧斯文
比起黄州、惠州,东坡在儋州词作绝少。张鸣的解释是,东坡到儋州后,与过去诗酒流连的生活方式不同,酒宴聚会少了,需要用词的场合也少了。确切地说,东坡寓居桄榔庵期间,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他念兹在兹的学术著作: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《书传》。
这些著作的写作,始于黄州。远离朝堂的喧嚣,苏东坡终于有了难得的治学时光。《易传》是他父亲老苏晚年未竟的事业,他在临终前还嘱咐苏轼两兄弟要最后完成。东坡在黄州一面整理父亲的遗稿,一面选取弟弟读《易》的札记,同时加入自己心得体会,编撰成书。于黄州期间,他也开始研读《论语》。他曾在《上文潞公书》中,称“到黄州,无所用心,辄复覃思于《易》《论语》,端居深念,若有所得”,又致信腾达道、王巩、李之仪等友人,称自己专治经书,一二年间,了却《论语》和《易》,又可作《书传》《书义》。
远谪儋州,东坡有了大量时间,借机修订在黄州期间写成的九卷《易传》和五卷《论语说》,另外新撰《书传》十三卷、《志林》五卷。《夜梦》一诗中,他犹能梦到儿时父亲责怪他读书不用功的情景,醒来依然心有惭愧。
东坡对这三部著作极为看重,写给朋友的信中,他说:“抚视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三书,即觉此生不虚过……其他何足道。”在张鸣看来,经学著作作为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载体,是当时新型士大夫最重要的学问,苏轼自然也不例外。
我曾以为,远谪岭海的苏东坡不再关心朝政大事,其实不然。张鸣发现人们只注意到苏东坡在惠州所写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其实他写于同时期的另外一首《荔枝叹》,更值得重视。“这是一篇被称为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作品,在这首诗中,他从历史上进贡荔枝的事情写起,批评汉朝、唐朝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的苦难,进而批评当朝进贡茶叶和牡丹。自注中他隐晦地写道:‘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,许之。’我要追问:谁许之?其实将批评矛头指向执政大臣甚至皇帝。”
自黄州以来,东坡一直保持着对陶渊明的喜爱,儋州期间他写了大量和陶诗。张鸣注意到其中一首诗《和陶咏三良》这样写道:“我岂犬马哉,从君求盖帷。杀身固有道,大节要不亏。君为社稷死,我则同其归。顾命有治乱,臣子得从违。”其中的政治态度,与他所坚持孟子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思想一脉相承。直到晚年,东坡在努力完成学术著作的同时,依然保持着对人生、政治的思考,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。
元符三年(1100)二月,苏东坡因徽宗即位大赦天下,得以内迁广西廉州。这一年六月二十一日,他离开澄迈海边驿站通潮阁,渡海而去,临走留给海南最后一首诗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?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通潮阁的遗迹早已不存,但在澄迈老城,尚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广德桥,据说这座桥正是东坡当年离开澄迈官道的必经之桥,不过当时是木桥而已。我们一路找到这座标识为“里桥”的古桥,桥上杂树丛生,残留的四孔桥洞满是斑驳,桥下流水形成的瀑布声闻数里。李公羽告诉我们,这里正是当年通潮驿的所在地,沿着驿站旁的河道,可以直通入海。据说,在不远处一个老糖厂的水塔,便是当年通潮驿中通潮阁之所在。
渡海途中,苏东坡遭遇风浪。据他在《志林·记过合浦》中的记载,当时苏过已经睡熟,他在急切中,手抚自己的三本著作,叹而祝曰:“天未欲使从是也,吾辈必济。”不久,果然风平浪静。
(本文写作参考王水照、崔铭著《苏轼传》、韩国强著《寻访东坡踪迹》等书。感谢荣宏君、韩国强对采访的帮助)